媒体解析转基因科普难 呼吁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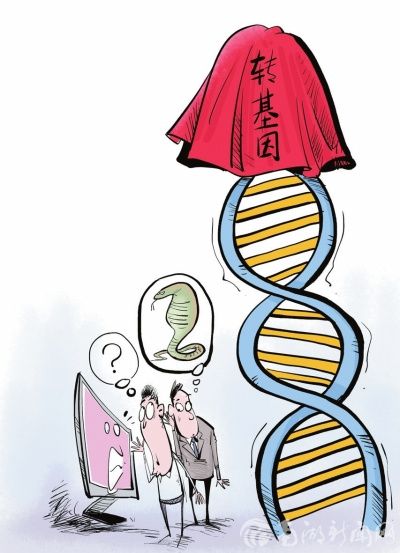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首次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而且,与往年的一号文件相比,“分子育种”的委婉表述被“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替代。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的鲜明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
事实上,各种转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进行,但整体看,这些脉冲式的科普活动并不系统,受众面有限,形式较为单一,因此成效并不明显。让很多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有些沮丧的是,猜疑、抵制甚至谩骂转基因的言论在网上一直甚嚣尘上。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转基因科普为何这么困难?
□转基因科普为什么难
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并不能决定转基因接受度
在谈论转基因科普前,不妨先换个问法,要不要转基因科普?之所以这么问,并不是让转基因科学家或相关科学界放弃与公众的交流,而是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传播研究者30多年来对转基因的研究表明,转基因争议是公众心理认知特点、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延后的传播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并不完全是由于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用高举“转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来促进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决方案——虽然现在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限于加强对公众的知识教育。而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并不能决定公众的转基因接受度,这几乎是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共识。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受众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其他学者则断定,与其说更高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
该如何理解知识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呢?心理学的认知原理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类认知能力有限。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好习惯”。无论如何,这些习惯让我们回避风险,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认知资源。
可回到转基因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不关心时,很难对他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普及了也记不住。但当各种有关转基因的负面消息充斥媒体或网络空间时,人们会迅速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这种态度大多时候是负面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做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不用说,在大多数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趋于固化之际,做出回避或拒绝决定的人不在少数。
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对转基因的接受度相关
2006年,一项关于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含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接受有明显相关性。
为何中国的研究结论会与前述知识作用有限的研究结论出入较大呢?原因之一是时间差异。对中国的研究,最晚在2006年进行,其时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尚未固化,知识仍有用武之地,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学历差异也代表着对科学界的信任度差异。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下,学历越高越容易信任科学家的工作。最近还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理工科研究生支持转基因的接近90%,原因很可能也在于此。
实际上,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
这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转基因技术而言,在公众认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如此一来,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
如果缺乏体制性信任,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就会明显降低。例如,19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将相同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信息拿给两组英国公众看,告诉其中一组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告诉另一组这是英国政府的结论。结果后一组对转基因安全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前一组。分析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疯牛病问题上隐瞒真相的结果。
除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尊重科学权威和信任科学家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非常重要。一项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亚人10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
总结上面介绍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公众的知识水平并不能确保他们接受转基因,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人们是否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相关性;相信科学权威对于人们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影响。
科学家对热点事件的回应,往往晚于媒体对它的报道
通过上述分析后,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把人们是否接受转基因的主因归结为认知习惯、信任与价值等心理因素,那就难以解释,为何其他的争议性科技没有像转基因这样遭到这么多非议?为何转基因议题在世界转基因研发与应用第一大国美国没有成为重大的争议甚至话题?
实际上,这又涉及社会体制与人类认知因素的互动。1990年代初期转基因争议初起时,欧洲以反核和反企业污染为标志的环保运动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很多环保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者亟须新靶点,转基因来得“恰到好处”。另一方面,科学家对与公众交流的轻视让他们迅速丧失了话语权,到2003年英国就是否让转基因产业化举行全国性辩论时,科学家和政府方面一败涂地。
但科学家的失败不都是因为他们放弃传播,转基因知识在舆论场的缺席,与科学共同体逻辑和媒体逻辑的错位有关。一项对近15年来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转基因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慢了一拍,错过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时期,相应地减少了公众全面获取转基因知识和正面信息的机会。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而生物技术公司要用低调避免争端引火烧身。结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的兴趣已经锐减,这导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中国转基因科研与产业界同样存在这种回避热点新闻的情况。
回溯中国转基因舆论的演变历史,很多人会想到一些媒体报道直指科学家因个人商业利益而力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些报道在价值立场上为读者构建了对利益勾结的控诉,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质询和抵制。而这种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公众对转基因知识了解不够,而是基于公众相信科学家具有商业私利,这破坏了他们对科学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价值认同,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而较弱的体制性信任又与较低的对新技术的接受度紧密相关。
正是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事件,使反对转基因的舆论经常占上风,并与人们心理认知方面的“偷懒”原则结合,在转基因问题上形成了公众舆论的固化。
□转基因科普该如何进行
开展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
上述分析表明,转基因争议的形成是心理认知、社会、政治、科学、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各种研究比较一致的一个结论是,知识程度不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
另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是,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中国的转基因决策尤为重要。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公众质询,透明度严重不足。殊不知,这只会恶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
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我们的转基因传播可在以下方面着力。
首先,研究结论表明,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程度更能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这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积极沟通,让公众通过对科学权威的信任转而更加理性地看待转基因问题,并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
其次,虽然知识本身不能改变受众的态度,但仍有必要坚持甚至强化传播正确的转基因知识。这一工作的目标不是要就此扭转公众的态度,而是要让正确的知识尽可能“占领”各种信源,让公众“启动”理性认知时可以找到正确的知识,也让非专业的传播工作者在传播相关知识时有据可依。
第三,科学家走出实验室,不仅是挤出时间多开几场转基因科普讲座或多发表一些科普文章。更重要的是,当公众关注转基因议题时——这通常是转基因争议再起或新问题出现时——他们要及时看到来自科学家一方的积极而理性的声音。
第四,要进行转基因科普,不能仅仅靠启动一批新的科普项目,更需要整个科研考评和科研组织体系的变化,将广义的科学传播工作以某种方式纳入科研考评体系。比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样,将特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一般不超过5%)用于科学传播。这能使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不再是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不能记录为学术成绩)的行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转基因议题已经超出科学本身,成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鲜活体现。只有积极开展各种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比如有关科学的听证会,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观点都占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参与并不能以牺牲科学真理为代价),才真正可能促进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
撰文 贾鹤鹏 范敬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