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科研伦理咨询能否排疑解惑
它们以一种并非由监管部门驱动的方式为科研伦理讨论提供开放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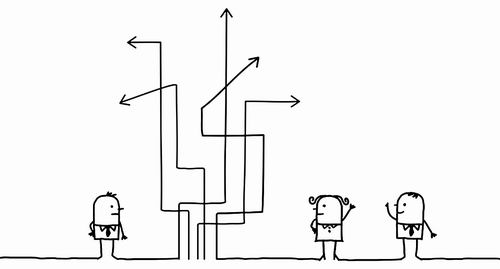
“我们不是道德警察。我们只是帮助科学家摆脱麻烦的另一个渠道。”图片来源:Nlshop/Shutterstock
当Stacy Hodgkinson和Amy Lewin招募一名15岁的怀孕少女参与研究时,他们绝对带有最好的初衷。两位心理学家正在评估一项针对年轻准父母的教育项目,而上述女孩符合所有的入选标准:头胎、孕期在15~32周、年龄低于19岁。更重要的是,并未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另一半愿意参与这项研究。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孩子的父亲已经24岁,根据当地法律,他会因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而犯下儿童性侵害罪。
很明显,这对夫妻在年龄问题上对彼此撒了谎,但却如实告诉了当时在华盛顿国家儿童医疗体系工作的Hodgkinson和Lewin。于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出现了。两位科学家已向参与者承诺为他们的信息保守秘密。然而,这是否可以凌驾于他们负有的向警方报案的法律义务之上?而这又将如何影响上述家庭?
“当时这位年轻的父亲告诉我们,他希望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与到孩子未来的生活。”目前在马里兰大学工作的Lewin说,向警方报案有可能害多利少。
为寻求道德和法律上的指导,Hodgkinson和Lewin联系了Tomas Silber。Silber是一名儿科医生,同时拥有一家研究伦理咨询机构,为一些棘手的研究问题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
对于Silber来说,解决方案非常明了,“你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向警方报案”。在向这对夫妻解释完自己的法律义务后,Lewin和Hodgkinson告诉了警方,相关调查也随后启动。这位少女和她的另一半与两位研究人员失去了联系,Hodgkinson并不清楚这位父亲是否在孩子或孩子母亲的生活中保持着正面形象,因为这是他们项目的最终目标。“有时候尽管你做了正确的事,但结果并不总是好的。”Silber说。
研究中遇到伦理困境并不是什么新奇事。富有新意的是科学家可以到正式的伦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不同于科学家通过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接受伦理指导这种标准方式,咨询公司可以提供不具约束力的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因为它们并不属于监管流程的一部分,所以能涉足更广范的问题,从知情同意和研究方案等琐事到类似实验性埃博拉疗法的使用等争议性问题,并且可以提供更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这种咨询机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科研伦理学家Joshua Crites表示,即使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有可能瞬间变得复杂,一群伦理学家共同努力解决问题最好不过了。
不过,很多科学家或者不知道有这类机构存在,或者害怕向它们咨询,因为这会为本已非常沉重的行政管理负担再添一道烦琐程序。今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放弃资助一个提供伦理咨询服务、为研究人员制定最佳方案的工作小组。
尽管财政支持会以某种方式重新获得,但伦理学家早已等不及了。来自西雅图儿童医院的Benjamin Wilfond成立了由35位生物伦理学家组成的临床研究伦理咨询协会。他们希望即使在没有NIH资助的情况下,也可以不断改善咨询服务模式。协会成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物伦理学研究所科研伦理学家Holly Taylor表示,他们对于继续开展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
咨询机构“乘虚而入”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人体试验都要经过IRB审批。现有IRB条例的基本框架出现在40年前。当时发生了一系列科研道德败坏行为,包括1932~1972年在亚拉巴马州开展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在该事件中,医生任由感染了梅毒的上百名非裔美国人病情恶化,并拒绝为其诊治。如今,IRB是在学术医学研究领域监督伦理行为的主要渠道。不过,它们的首要功能是确保科研工作遵循管控和法律要求。同时,其成员并非都具有生物伦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关于伦理学的讨论采取就事论事的形式,缺乏经过深思熟虑的系统安排。
于是,咨询机构“乘虚而入”。不同于IRB,这些机构可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提供指导,而不只是监管审查阶段,并且以一种非对抗性、提供建议的方式进行。用NIH临床中心生物伦理学咨询机构主任Marion Danis的话说:“它们以一种并非由监管部门驱动的方式为科研伦理讨论提供开放的空间。”
1996年,NIH临床中心在美国最早成立了科研伦理咨询机构。接下来的10年中,一些学术医学中心效仿其做法,纷纷成立相关机构。2006年,NIH发起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项目,强调药物研发和测试的学术背景。根据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到2010年已有30多家学术机构设立科研伦理咨询组织。然而,报告同时指出,去年接到研究人员电话寻求建议的咨询组织不到半数,而且只有6家全年接到的电话数超过10个。“在多数地方,咨询量最终都不是很大。”医学伦理学家Steven Joffe此前在哈佛医学院主管的一家咨询机构中非常清闲,直至2013年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时,情况才有所改观。
单独咨询服务有无必要
当然,早在NIH成立正式咨询机构之前,生物伦理学家数年来一直在提供关于科研的咨询建议。在美国之外,伦理咨询多数通过类似于IRB的机构进行,或者以非正式谈话和“路边咨询”的方式开展。“总的来说,它们都很随意,而且非常不正式。”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伦理学的专家Mark Sheehan表示。
在加拿大,关于科研的伦理建议还可以通过帮助病人和医生解决临终决定和其他道德问题的医疗卫生机构获得。不像美国针对科研伦理和临床伦理的培训项目通常分开进行,在加拿大“我们往往会获取到上述两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多伦多康复研究所生物伦理学家Ann Heesters表示。这是加拿大唯一一家宣称可为研究人员提供伦理咨询服务的医院。据Heesters介绍,她接手的咨询案例中每7个就有1个与科研相关。
在澳大利亚,“科研人员在提交正式伦理审查的全部申请之前很难寻求到建议。”在昆士兰大学研究科研伦理和法律的Nikola Stepanov介绍说。而一旦相当于美国IRB的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在某个研究协议中发现了伦理问题,研究人员便可能会在寻找提供进一步指导的正式渠道上遇到麻烦。
不过,并非所有的伦理学家都认为需要设立单独的咨询机构,即使是在美国。“如果IRB承担了伦理审查任务,为什么还要将其他人拉进来?”波士顿儿童医院临床研究社会责任中心主任Susan Kornetsky表示。而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致力于科研伦理和法律问题研究的Norman Fost更希望看到生物伦理学机构被并入IRB正式架构。因为IRB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的关卡”。Fost表示,这些原则上拥有高素质伦理学家的机构应当“审视每一份协议,找出其他人尚未发现的问题”。依靠一个单独、随意的咨询机构,意味着有些问题会被错过。
科学家真的会购买?
拥护者认为,咨询机构的目的是补充IRB和其他监管机构无法提供的服务,而不是与后两者融合。
Wilfond一直致力于提高伦理咨询机构的可见度和严谨性。去年,他和Taylor在《美国生物伦理学杂志》上发起一项名为“科研伦理上具有挑战性的案例”的系列调查。最新的案例来自Silber和他的同事。他们表示有向警方报告法定强奸幼女罪的义务。同时,Wilfond还在收集关于咨询机构的描述性资料,并在华盛顿大学扩展了业务范围,即欢迎学术界以外的咨询请求,包括通常雇佣律师大军而缺少生物伦理学家的制药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大学采取按服务收费的方式:对于制药公司,每小时的费用为200美元;对于非营利性机构,收得会少一些。
Wilfond和同事希望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开始发现咨询机构的好处。“一直以来,对于科研伦理咨询机构重要性的认识都非常不足。”马里兰州一家临床和科研生物伦理学机构咨询人员Charles MacKay表示。
“我们不是道德警察。”迈阿密大学伦理咨询机构联合主任Reid Cushman说,“我们只是帮助科学家摆脱麻烦的另一个渠道。”(闫洁)
《中国科学报》 (2014-10-30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