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在“反”与“挺”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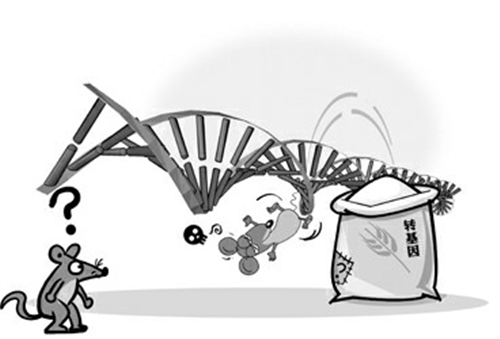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最近表示:转基因研发要积极,推广要慎重。2013年5月起,国内“挺转”人士在全国29个城市举办了30多场转基因食品试吃会;9月,方舟子和崔永元围绕转基因开始了不断升级的舌战;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透露,61名院士曾上书高层,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技术产业化;2014年1月,84岁的袁隆平在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后,对媒体表示“将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鏖战多年的转基因争论,由于种种原因,突然间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在国外,2012年法国《食物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长期食用转基因玉米会导致小鼠乳腺癌,相关图文被各国媒体广泛转载,两周后欧洲食品安全局紧急举行了大规模的专家讨论和评审,结论是这篇文章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可信度,而且存在很多硬伤;就在今年,一边,英国的一名环保人士为反转基因向公众致歉,另一边,欧洲议会刚通过了一项反对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决议,原因则是转基因玉米“先锋1507”的“抗虫花粉”可能伤害一般的蝴蝶和蛾,并且大多数欧洲消费者也不认为基因改造食品安全。
转基因究竟安不安全?围绕着转基因的种种争议又从何而来?当越来越多的公众陷入纠结的舆论话语场,难辨方向之际,有一种声音认为,在“挺转”与“反转”之间,最好还是少一些非理性的舌战,多一些心平气和的探讨,方为真正的科普之道。
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
公众所最为关注的转基因问题,莫过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大多数生物学家看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博士、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现在美国食品行业从事研发工作的云无心就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可信的。在他看来,科学上对转基因的认知,和公众对它的需求之间差别很大—从科学角度而言,经过风险评估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和相应的非转基因食品安全系数是一样高的;但公众期望的则是,必须经过几代人的食用,有足够的经验证明转基因食品没问题才是安全的。
正 生物学家眼中的转基因:安全性可以得到证实
公众对转基因的安全性期望并不理性
云无心认为,这样的公众期望并不理性,从科学而言也不合理。事实上,科学认知中的关键词“风险评估”并不为绝大多数公众所理解。在风险评估中,转基因食品只要证明和相应的非转基因食品风险相等,即是安全的,并不用证实其绝对安全性。因为从逻辑上说,一个东西的绝对安全是无法证明的。
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一个关于风险评估的指南。首先评估的是基因的来源。转基因不是随意地将猪的基因转到牛的身上,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如果基因来源被发现是某种致病细菌,就不能使用。其次,基因在转入之后,还要考察表达产物是否安全。比如Bt基因的表达产物是Bt蛋白,那就需要确认它在被人的胃肠消化后,不会像被虫吃了之后那样,被激活产生毒性。
同时,云无心指出,仅仅证明Bt蛋白是安全的,还是无法证明含有Bt蛋白的产物是安全的。Bt蛋白的安全性仅是转基因产品安全性证明中的一步,之后还得进行代谢产物的评估。某个基因转入之后,增加或降低某种代谢成分可能会影响到作物的代谢途径。事实上,这在风险评估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叫做非目标变化的评估。
非目标变化,指的是在转入某个基因之后,该基因可能将别的要表达的基因沉没掉,或是将另一个本来不表达的基因激活,或是影响了别的基因的表达。所以,这些非目标变化的评估在转基因安全风险评估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云无心解释,非目标变化事实上有利有弊,因此如果发生了这类变化,就需要评估出变化是好是坏。并且,该检测应当从项目起始就进行。在一个真实案例中,由于某个转入的基因来自于花生,而花生是一个常见的过敏源,因此在进行评估之后,该转基因项目就中途夭折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评估是营养组成,包括对矿物质、脂肪酸、氨基酸等等进行评估。在转基因食品评估中,会将非转基因品种和进行转基因操作后的品种放在同样的生长条件下进行营养组成的比较,其结果必须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才能被接受。
风险评估是两条针对转基因食品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另一条则是个案审核。
个案审核的第一层意思是,只有通过审核的转基因食品才被认为是安全的。在中国,食品要拿到农业部的安全证书,才被认为是可以安全使用的。其次,“个案”的意义在于,不管发展了多少年,即使已经有无数的转基因产品获得批准,下一个新的转基因产品仍然要经过审核。同时,如果真的发现某一个产品是不安全的、有问题的,那也只表示这个产品自身有问题,而无法就此推翻转基因产品整体的安全性。
通过几代人食用证明食品安全性并不靠谱
在转基因安全审核中,动物试验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云无心指出,其实在转基因安全评估中,是不要求动物试验的。原因在于,如果用动物试验做表达产物的安全性和致病性的检测,可以用十倍百倍剂量的纯蛋白去喂,然而,成品粮食由于喂食剂量有限,因此在动物生长过程中,会被其他的影响因子盖过,这将导致动物试验出现偏差,难以得到准确结果。
最后,通过几代人的食用来证明食品的安全为什么不靠谱呢?云无心表示,因为如果食品只有轻微问题,即使经过几代人食用都检验不了。举例而言,咸鱼直到近代,依靠流行病学家的统计、假设,和毒理学分析,才被发现对鼻咽癌的发生有绝对影响。而如果一种食物有比较明显的毒性,那也用不着吃几代人,通过毒理学试验早就发现了,甚至只是通过成分的比较就能发现。
云无心认为,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来源于对“人工的、非天然的”食物的不信任。但换个角度看,转基因只不过是一种育种手段,而所有的育种手段,要产生新的品种,必然要改变基因。迄今为止历史上有过四种育种手段,第一种是自然选育,大家到野地里看运气,是靠大自然中发生突变保留下来,你喜欢的性状也是选择的结果。而现在使用的大量的诱变育种,不管是用辐射还是化学试剂,都是非常随机地改变了基因,并且是不可控的。杂交育种相对于诱变更可控一些,但它也只是使用两种基因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而转基因中出现的使一个基因的表达改变,这在任何一种育种手段中都有—转基因广义而言,只是一种基因改造而已。
反 生物学家眼中的转基因:安全性可以得到证实
不过,也有一些相关领域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郑风田就对记者说,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有所担忧,是可理解的。因为历史上,有好几种食品,都是在吃了一二十年之后才发现了副作用。他举例说,比如瘦肉精,作为一项新技术,用了20年,直到在西班牙出现了集体中毒事件,才发现瘦肉精原来是有害的。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的一个医药公司研发了一种缓解更年期症状的药物,过了几十年后才发现,使用该药的妇女得卵巢癌的比率要高很多。
郑风田因而十分反对转基因试吃活动,他认为这对公众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就像抽烟,抽一两根,会立即有作用么?”在他看来,由于长期动物试验的缺乏,转基因的副作用其实仍然无法完全被否定。并且,在中国,消费者眼中的转基因食品往往会和另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挂上钩,因而对其感到恐慌。郑风田认为,当公众对食品感到不信任,那他就有权力选择不吃。从这一点而言,崔永元并不是反对转基因本身,而是要肯定选择权。
“转基因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郑风田说,现在不论是“挺转”,还是“反转”,都有非理性的趋向,“挺转的许多都是学生物学的,用他们的逻辑来看待事物;而另一波反转的则抱持着阴谋论不放。”郑风田对转基因的态度则是,技术上研究,商业化慎重。
“例如,作为中国人主粮的大米,就不能轻易动。同时,如果中国农民全部种上转基因粮,不可能全部进行标识。”郑风田表示,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的做法,在转基因食品的商业推广上谨慎为先。
生态环境影响惹争议?
公众和业内人士关心的另一个重要的转基因问题是,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由于转基因是人为地让一个基因在其非自然的时间、地点、环境进行非自然的表达。因此可以说,任何一个转基因生物都有可能对其所在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有害的,但也可能是有益的。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般经由转基因本身的表达,转基因的意外逃逸对目标物种施加强大的非正常选择压力,或是对非目标物种的意外伤害等途径而实现。转基因生物本身也可能脱离管控进入自然界,进而成为杂草或其它侵袭性生物。其害处在于,可能造成目标种群抗性的出现,以及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下降。
正 生物学家眼中的转基因:安全性可以得到证实
在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看来,几大关于转基因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和解答。专家们的意见是,对于生态环境,转基因利弊皆有,关键还是看如何制定适宜策略,扬长避短。
转基因对非靶标生物会否产生影响?
抗虫转基因能使受体植物(如棉花、水稻、玉米等)产生杀虫蛋白,如转Bt抗虫转基因的棉花和玉米,具有杀死棉铃虫和玉米螟虫等棉花和玉米主要害虫的能力,这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降低了化学农药的使用而带来的生产成本和生态影响。
而且通过研究的比较分析表明,由于Bt蛋白只是对鳞翅目的某些昆虫具有攻击的“靶点”,所以只对棉铃虫、玉米螟和水稻螟虫等鳞翅目的害虫有明显杀灭作用,而对非鳞翅目的昆虫(包括害虫)和蜘蛛、天敌昆虫和节肢动物均没有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种植对生物多样性会否产生影响?
转基因作物在全球的种植面积从1996年规模化进入商品生产以来,短短17年中就增长了100倍,达到1.7亿公顷面积,这个面积相当于英国国土面积的6倍。由此产生了两种担忧:其一,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是否会令农民放弃自己的传统农产品(000061,股吧),而选择大量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二,当转基因作物品种中的个体通过人为混杂的方式或基因漂移,混入非转基因品种中,由于某些转基因具有自然选择优势而被保留下来,传统的非转基因品种则逐渐被淘汰。
卢宝荣称,其实,第一种情况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发生过。当时,在半矮杆基因资源利用和遗传改良技术带来的“绿色革命”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高产作物(如水稻、小麦和玉米)品种,这些高产品种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另一方面,农民也因此放弃了对传统农家作物品种的种植,从而致使许多地区的传统品种丧失,也带来了之后对传统农作物品种的保护策略的诞生。
其实无论是“绿色革命”产生的高产品种,或是“基因革命”产生的高产、优质的转基因品种都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和更强的生命力。它们带来的品种多样性下降问题,可以通过政策以及对品种种植的合理布局来解决,而不是摒弃这些优良品种。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有效管理,以及在转基因品种和非转基因品种之间设置一定的空间隔离距离来达到降低和避免基因漂移而导致的转基因混杂。
转基因对土壤生物群落是否存在潜在影响?
转基因作物进入大规模的商品化种植,其根部的分泌物、残留在土壤中的转基因作物根系、凋落物和未被收获的作物残留部分进入土壤后,是否会对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小型动物产生负面影响?残留物在土壤中分解的过程中,是否会影响土壤的生态性能及功能?
卢宝荣表示,针对这一问题,科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含有Bt转基因残体的土壤中虽然能检测出一定量的Bt基因或Bt蛋白的残留,但这些残留物对微生物和小型动物均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
反 “超级”杂草或昆虫 现在一说起基因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谈到所谓的“超级”杂草或昆虫,这是因为目前在生产上使用最多的,是抗虫的Bt转基因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
所谓“超级”,是指它们具有其同类本不具有的抗特定除草剂或杀虫剂的能力。也就是说,本来可以杀死它们的除草剂或杀虫剂对它们再也无效。由于它们的一般同类都被该除草剂或杀虫剂消灭了,无其它草或虫与它们进行生存竞争,可以取得尽量多的营养和生存空间。于是,它们就可自由生长,而且长得特别快也特别大。
这些“超级”杂草和昆虫的产生,其实同生物进化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是在一个地方长期大量使用单一抗除草剂或抗虫转基因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生物种群里,由于遗传变异的积累,都存在一定的基因型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生物种群适应不同生长环境,抵抗灾难的法宝。生物进化的基础是物种本身基因型的多样性,而生物进化的推动力是环境对这些基因型的选择。
如果使用转基因生物的目的是对另一种生物(一般称为“目标生物”)进行直接(如抗虫)或间接(如抗除草剂)的伤害,就等于是对该目标生物的基因型进行一种选择,从而使目标生物朝向抵抗伤害的方向进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选择压力。也就是说,目标生物中,能被杀死的都被杀死了,只剩下杀不死的。结果就是使原本在群体中并不占优势的抗性基因型变成了优势基因型。该转基因的表达强度越高,表达的时间越长,该转基因生物的群体越大,这种选择力度就越大,具有抗性的目标生物就会越早出现。
例如,Bt杀虫剂在Bt转基因棉花问世以前就在棉田使用了很多年。但由于成本原因,施洒强度有限,没有对棉田周围生物多样性造成明显影响。
但是,在Bt(Cry1Ac)棉花于生产上大规模应用六年后,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和阿肯色州的数十个Bt棉田里,就陆续发现该Bt蛋白杀不死的螟蛉虫。而且,这些抗Bt的螟蛉虫的群体增长迅速,很快就蔓延开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Bt棉田里,2010年也出现了抗Bt的螟蛉虫。
另外,毒杀西部玉米根虫的Bt(Cry3Bb1)转基因玉米,在美国爱荷华州和伊利诺伊州一些农场连续种植三年后,田里就出现了Bt蛋白杀不死的西部玉米根虫。同样,近年来在美国不少地方,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也因大量施洒同一除草剂,而在连续几年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或棉花的地里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