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回眸:记者眼中的2016
编者的话
过去的一年,是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科技政策密集出台、科学争议此起彼伏、社会热点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年。《中国科学报》的记者也经历、见证了国家、社会改革前行、创新发展的点点滴滴。在用笔、镜头记录当下发生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留下了自己独有的印记。大事小情、热点难点,感动并触动、质疑或深省,我们希望通过撷取个人的一些经历,夹叙夹议、有感而发,能够以微观的视角还原一些重大热点事件的另一个侧面,进而再次描摹过去一年社会进程中的某些显著特征,特别是科学发展的一些时代特征。个人视角的叙事,兼顾对于国家层面的响应。2016,我们深切回眸;2017,我们深情寄望。

①10月17日凌晨4点多,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前,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出征仪式上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报告任务准备情况。王佳雯摄

②10月17日,搭载着两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一号伴随着“点火”口令的下达,成功点火,现场瞬间腾起火红色的烟雾。王佳雯摄

③2月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搭载着新一代北斗导航系统的第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倪思洁摄

④7月3日,FAST工程主体完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工程项目办供图

⑤4月6日凌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搭载着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拔地而起。
倪思洁摄

⑥诺奖得主内尔走进中科院附属实验学校。

⑦云南扶贫调研之三七种植园。

⑧2016全国双创周上的3D建模试衣间。(图⑥⑦⑧李晨阳摄)
2016,我的工作记忆从引力波开始
■本报记者 王佳雯
北京时间2016年2月11日,国人还沉浸在春节阖家团聚的喜悦气氛中时,大洋彼岸,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负责人David Reitze通过一场激情洋溢的发布会,搅动了整个物理学、天文学界。他骄傲地宣布,“我们发现了引力波!我们做到了!”
如今,近一年的时间过去,回望2016,在LIGO引力波成果背后涌动的兴奋与躁动、期望与质疑正慢慢趋于理智与平静。可喜的是,无论引力波研究受关注与否,科学的进步已矗立在那里。
LIGO引力波探测的结果,犹如在相关研究领域投入了一颗重磅石子,在科学界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并迅速扩散至中国。我在采访中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相关研究人员的喜悦。当然,他们的反应也是迅速的,在为大众解读成果的同时,也顺势推出了国内的相关研究项目——天琴、太极、阿里等一系列引力波研究计划最先走进人们的视线。
这些项目研究手段各异、科学目标也不尽相同,可以说,中国的相关项目与其他国家已铺设的项目联手,力求将引力波这一宇宙乐章的高、中、低音区全部覆盖。这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关于宇宙起源研究的盛大演出。
此时,争议也你推我搡、毫不示弱地涌了过来——我们的科学研究是否在跟风?上马的科学计划是否存在重复?又是否会带来资源浪费?
在近一年的观察中,我渐渐觉得,国内一系列的动作与其说是跟风,不如说是“借东风”。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科学家在相关领域多年的探索与积累是不容忽视的。
在中国科大的一次采访中,一位老科学家向记者讲述了上世纪末在实验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中国科大、北师大等科研院校老一辈科学家所进行的持久而深入的理论探索。这次采访也让我明白,如今红火的国内引力波研究项目并非空中楼阁。
此后,我还有幸拜访了中科院一位海外归来的学者,他讲述的早年间于赤道附近所进行的引力波探测实验,令我印象深刻。虽然实验最终并未成功,但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探索,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前辈的积累,无疑是如今国内引力波研究快速发展的基石。凝聚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未知前方等待的是否曙光,需要漫长坚守的这一领域,能够借助这一成果获得更多重视与支持,甚至让那些被迫放弃研究的科研人员重获“生”的希望,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今年3月,我在参加一场引力波研究的学术会议时,一位年轻科研人员在报告中曾打趣地说,LIGO救了自己的饭碗。原来,在LIGO宣布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之前,他所从事的引力波相关研究因探索时间长、成果不可预期等因素而不被看好。他一度被建议,该换个领域寻求突破。好在LIGO这场春雨来得及时,让这位年轻科学家的研究得以继续。而他的经历成为我2016年想起引力波研究时挥之不去的一幕。
如今看来,这位青年科学家的经历,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好在对国内的引力波研究而言,情况正在改善。
8月,《中科院“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在发布会现场,当看到为研究宇宙起源等提供基础的星系结构、形成与演化被列为60个有望实现创新跨越的重大突破之中时,我内心感到十分欣喜。这意味着未来5年,天文学、物理学的发展值得期待,而引力波研究自然也会从中受益。
之后不久,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竣工。这只能够捕捉遥远星辰最细微“声音”的巨型“耳朵”,又为利用脉冲星探测引力波增加了砝码,也让我看到国内引力波探测的布局正日趋明朗。
佳音频传。12月中旬,我一直跟踪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计划”终于正式启动,计划5年建成开始科学观测。自然,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科研力量投入到这一领域,但“阿里”的成功上马,却可以为我心中轰轰烈烈的2016“引力波年”画上一个无憾的句点了。
回望2016,引力波研究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期盼与质疑的目光。而科学的进步在涌动的潮水退去后,终将显露出令人欣喜的本真之色。我也期待着,下一个引力波研究成果,如冲击波般再次席卷全球,也期待着,在下一次引力波浪潮袭来之时,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将展露锋芒。

王佳雯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采访当地百姓,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后他们生活发生的变化。
改革恒久远,“抱怨”永流传
■本报记者 倪思洁
“垃圾!只会数论文的评价,简直就是垃圾!垃圾!”
当我照着预先设计好的采访提纲,与德国马普所等离子体中心的克雷伯教授聊起德国科研体系及评价方式时,教授放下手里一直端着的马克杯,在靠背椅里直挺挺地坐了起来,瞪大眼睛,提高声调,几乎要失去了风度。
教授的激动,让“唯恐天下不乱”的我也兴奋起来。让我“暗喜”的是,原来,科学界的“抱怨”不分国别!
从前,我总以为国外科研环境好,国外科学家生活惬意。直至此时,我由衷感慨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总结出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多么智慧。当我用这句中国俗语来安慰克雷伯教授时,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们中国,正在尝试改变。改变,意味着希望。”
确如克雷伯教授所言,2016年,我国科研环境发生了频繁且深刻的变化。“松绑+激励”已经成为2016年中国科研环境的关键词,这样的变化,让国内科研人员备受鼓舞。
今年5月,科技三会的召开为“给科研活动松绑”奠定了基调。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从经费比重、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为科研人员“松绑”的措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让科研人员“回归科研本位”。松绑之后,“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了,人员劳务费没有门槛限制了,差旅会议费用有更大的自主权了。
2016年,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注入了更多动力,这些也让混迹于科研圈的我,在国际友人面前倍感骄傲。
2月,国务院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印发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加大源头供给,促进研发机构、高等院校技术转移;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创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良好环境……科技转化政策更加细致,政策实施更接地气。
3月,财政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政策向全国推开,国有科技型企业可以面向企业重要技术人员实施股权出售、股权奖励、股权期权等股权激励办法或实施项目收益分红等激励办法。
9月,国家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和相关获激励者的税负。
激励之下,中国科学家辛苦摸索出的科研成果不用担心被“贱卖”了,创新创业不用担心身份尴尬了,拿到手的奖金不用担心扣税太多了。
就在我从德国调研采访回来之后,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让知识的价值得到了认可,让长期以来智力劳动与收入分配不相符合、内部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了解决方案。2016,真正成为知识和人才的价值得到更充分体现的一年。
不过,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至今记得,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我与年轻的科学家冯克教授在中餐馆吃晚餐时,他向我抱怨了德国科学家遇到的束缚:“我们也做过改变,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听罢,我玩笑着说:“改革恒久远,‘抱怨’永流传。”教授大笑:“正解!”
改革,永无止境。科技体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新年来临之际,我由衷地希望,2017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走得更顺更稳,科研人员创造力能得到更彻底的解放,中国科学家的腰杆能挺得更直、更硬。

倪思洁在FAST工程主体完工现场。
为科学家“网红”点赞
■本报记者 陆琦
“啥也不说了,快进来点赞!”2016年12月初,记者的朋友圈被一项网络投票刷屏。
作为中国科学传播的一件年终大事,“典赞·2016科普中国”征集网友投票点赞,投票结果将作为2016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物、十大科学传播事件、十大“科学”流言终结榜以及十大优秀科普作品终评的参考。
在“2016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物”的入围人选中,有几位早已是拥有大批“粉丝”的科学家“网红”,比如“春哥”郑永春,热衷“小”科普的大院士金涌、刘嘉麒……
2016年8月,因为采写“聚焦科普人的烦恼”系列报道,记者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这几位superstar(超级明星)。
采访金涌的时候,这位81岁的化工专家还不知道自己“火”了——因为拍了套科普“大片”而成为2016年的“网红”大院士。
由他担任总策划的《探索化学化工未来世界》系列科普视频问世短短两三个月就有点儿供不应求了。从大学生到中学生,从化工企业到中小学校,来自各方面的需求在金涌秘书的笔记本上记录得满满当当。
上面还记录了一些“粉丝”的反馈,令记者印象深刻:“从科学和工程前沿的全新视角,看到不一样的美丽化学和美丽化工”“像美国大片一样,让人看后心潮澎湃”……
想不到的是,这10部10分钟的视频短片及配套科普书,竟耗费了金涌和他的团队整整6年的时间。找经费、找专家、策划选题、编写脚本、指导制作、撰写书稿……金涌愣是将这件“讨人嫌”的活儿做了下去,只为了向公众展现出一个真实而美妙的化工世界。
尽管要实现科研与科普“双翼”齐飞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令人欣喜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看作是自己的天职。
“我要当网红!”郑永春从不掩饰想成为明星科学家的愿望。而事实上,郑永春近一两年频繁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似乎已习惯当一个明星科学家。
主要从事月球与行星地质研究的郑永春,热爱科普。他撰写了科普文章200多篇,作科普报告100多场。他在机场等了9个多小时也没有因为大雨而改变行程,只为了能给山东大学的学生作一场题为《人类走向深空》的科普报告。
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最简单的话:“有人想知道,我就要讲。”
因为这份热情,美国天文学会将2016年的卡尔·萨根奖授予郑永春,以奖励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郑永春成为首获此奖的中国人。
不过,在中国,想当科普“网红”的科学家少之又少。记者在朋友圈简单作了一个调查:你做过科普吗?结果得到的科研人员回复大多是否定的。
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做科普是小儿科,是大材小用;还有些科学家认为,科学家做科普是不务正业,科学家应该全心全意做科研。以上两点也是媒体和舆论的主流观点,导致很多科学家有兴趣做,但不敢去做科普。
这一点在一位采访对象身上得到印证。该大学教授在科学网开设了博客,非常活跃,博文写得好,“粉丝”也不少。但在“圈里人”看来:本来他可以出顶尖级的科研成果,但就因为在科普上花的时间精力太多,导致科研停滞了。这位教授自己觉得做科普很有意义,但大多数同行却表示“为他可惜”。
这其实是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很多尝试做科普的科学家,在不受认可的大环境中最终选择放弃。说你是为了出名,不好好搞研究,谁还愿意做?
科学家很少能从科普中获得物质奖励,做科普的动力往往源于自身的责任感和来自受众的成就感。但对于最重视声誉的科学家来说,这样的动力常常敌不过科学界的不理解带来的压力。
前不久,记者在一次科普活动中再次遇到金涌,询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告诉记者,还在忙活《探索化学化工未来世界》系列科普视频的第二辑。“等我这20个片子做完了,再找一些年轻科学家来挑头做30个、40个……”金涌坚信,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进行科普宣传的责任,因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如果不能把科学新发现传递给孩子们,使他们热爱科学,谁来成为我们国家未来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呢?
想到这儿,记者不禁为这些科学家“网红”再点上一个赞。

陆琦在神农架金丝猴科普基地采访时偶遇呆萌的川金丝猴。
对撞机“论战”有利于公众了解“真科学”
■本报记者 甘晓
超级对撞机,是全世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作为科学记者,我也非常关心。
2012年7月,我为参加欧洲开放科学论坛在都柏林机场过海关时,海关工作人员问我:“此趟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我答:“我是科学记者,来报道欧洲开放科学论坛。”他微笑了:“那你一定知道激动人心的希格斯粒子!”
此前,欧洲核子中心(CERN)刚刚宣布,他们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s)。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当“Higgs bosons”从一个普通的海关工作人员嘴里吐出来时,我还是感觉有些惊讶和感慨。随后几天,CERN主任Rolf-Dieter Heuer不仅在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还让加速器、对撞机在都柏林火了一把。我甚至亲耳听到都柏林的大街小巷都在谈论Higgs bosons。
后来,随着对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不停思考,我时常回忆起这一段段与高能物理有关的日常对话。我想,让我产生如此感触的并不在于都柏林人对高能物理掌握的知识比我们更多,而在于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普通人愿意谈论并且支持科学。要知道,在中国,和大多数科学研究领域一样,高能物理被紧紧关在一个个闭门会议中。
事实上,因为职务之便,我了解到,从2012年开始,中国科学家对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和高能质子对撞机(SppC)就开始讨论,并且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并且,在2015年下半年、2016年下半年召开的两次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尽管政府拨款进行CEPC预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决策的态度。
然而,这样的分歧依然在不公开的场合存在。
直到2016年,关于“中国该不该建造超级对撞机”这个本属高能物理领域的专业问题,突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许多完全不懂高能物理,甚至不懂科学的网民,竟然在网络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个现象一定是可笑的:非专业人士有什么资格对科学决策指手画脚?然而,我却认为它是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著名物理学家、94岁高龄的杨振宁公开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用七条理由反对了此前数学家丘成桐的“几点意见”。一天后,杨振宁的文章便受到了正在大力推动中国建造超级对撞机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的逐一反驳。随后,王贻芳的论述,又遭到了曾参与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项目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孟源的反驳。
专家们的论战对对撞机的科学目标、花费以及将产生的附加效应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此前写在从未公开发布的项目书中的内容,以一种愿意被读者理解并试图说服读者的方式,尽可能地广泛传播着。
人们开始了解,对撞机建造是一项昂贵的工程,花费的是源于纳税人的政府财政,它到底值不值,和所有人的利益相关;人们开始了解,中国科学家计划建造的是一台超级大的机器,将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引领全世界科技发展,这是国人值得骄傲的事;人们开始了解,就算是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家,对正在预研的下一代CEPC和更遥远的SppC意见也不统一……
岁末年初,争论仍然没有结束,并因为“论战”变得公开化。
在我看来,这场对撞机论战更大的意义似乎远不只为科研决策提供更多思路。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了解并支持科学。多年来,中国的科学传播一直停留在单向、线性的模式中,即科学家讲什么老百姓听什么的阶段。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和媒体本能地将科学“包装”成完全正确的、完美的事,但这不是真实的科学。
老百姓对科学家工作的了解只停留在片面,无法全局掌握,更鲜有独立思考和判断。尤其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人们接收信息方式的今天,人们对“真实”的需求更胜一筹。如果没有“真实”的科学,公众何谈支持?
今年的“对撞机论战”中,正反双方直接摆出了花费大价钱修建大工程的各种层次上的利弊,这在中国任何一项大型工程中都没有先例。毫无疑问,这项“和万里长城一样引人瞩目”的工程在讨论中变得透明而真实,让未来的科学决策变得日益公开,让公众了解不那么完美的“真科学”,才能让更多人支持、热爱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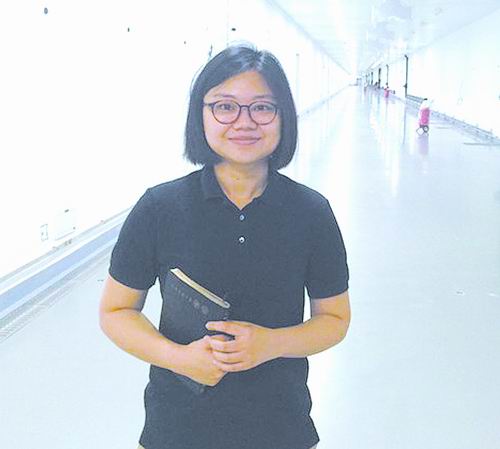
甘晓在上海光源新建的一个隧道里。
从“老兵传奇”看学科交叉
■本报记者 陈欢欢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衍达的学术生涯颇有点“传奇”意味——他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研究所创建人,却并非生物专业出身,本来的专业电子电路,赴美留学后转为信号和信息处理,60岁时突然跨入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生物学,成为我国生物信息学的先驱。
这样一位在学科交叉领域里游刃有余的“老兵”,自然是每个科学记者都不会放过的采访对象。因此,当我在今年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信息学部分会上看见李衍达院士时,首要任务就是在会后“盯住”他。
不过,会议尚未结束,另外两位绝佳的采访对象又浮出水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激光医学科主任医师顾瑛和北京大学教授杨芙清。这两位,一位是新晋院士,一位是资深院士,除了都是美女院士,其共同点是,都在院士大会上为学科交叉融合振臂高呼。
在我多年的科学新闻采访经历中,曾经接触过多位交叉学科的科学家,他们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乐在其中”。因为学科交叉点往往是新的科学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交叉科学是综合性、跨学科的产物,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从事交叉科学的科学家在品尝到了学科交叉带来的“甜蜜”之后,都对此乐此不疲。
不过,学科交叉要求科学家本人具有多学科的学科基础,如何在各学科间做到游刃有余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对于刚刚尝试学科交叉的年轻科学家,往往会被所谓的“门槛”迷惑。因此,如此“巧合”地碰到三名交叉学科的院士,对记者来说真是机不可失,他们的学术经历也许颇具标杆意义。
幸运的是,通过各种努力,我最终顺利采访到了这三位风格迥异、各有特色的学者。
在我看来,顾瑛像一名“斗士”。“信息学部能选择激光医学,我感到这个交叉学科的春天来了。”在会议发言中,顾瑛真情流露。院士大会期间,她抓住各种机会同其他院士交流:如何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解决临床医学中的难题。顾瑛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她时刻能感受到患者对医学科技进步的迫切需求,然而面对众多医学难题,单靠临床医生很难解决,必须联合其他学科的支持力量。
在谈到医学同其他学科交叉的困难时,顾瑛快人快语:“我们团队30年才做出一点成果,长期没有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我作为临床大夫还可以看病,但对专职科研人员来说就太艰难了。”在采访中,记者无时无刻不被顾瑛的决心和精神所鼓舞。
相比而言,杨芙清院士更像一名“智者”。当听说记者想采访学科交叉的内容,她推迟了午饭时间,认真地拿出笔记本逐条向记者说明。尤其是总书记历次对科技发展的讲话,杨芙清精心总结、如数家珍。
“看过电视剧《陆军一号》没有?”她饶有兴致地问记者。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杨芙清哈哈一笑:“你去看看嘛,我看了三遍!”
杨芙清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学院里所有老师“补课”。原来,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两军交战,失败的一方请教“成功秘诀”,获胜一方拿出3个鸡蛋打破在一个碗里,代表其麾下的3个不同兵种融合在一起统一指挥。在杨芙清看来,这和总书记提出的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思路一致,对我国现阶段高校人才培养具有指导意义。
更令人敬佩的是,84岁的杨芙清也是“行动派”,其所在的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已经在第一时间根据“十三五”规划调整了专业方向。

陈欢欢在“科技三会”现场写稿。
仍记得那个无比温柔的拥抱
■本报记者 丁佳
“蹬、蹬、蹬……”踏着金属楼梯,我登上了停靠在海南三亚救助局码头的一艘大船。这艘巨轮,刚刚在马里亚纳海沟完成了52天的首航,创造了中国海洋科技发展史上的一项新纪录——它实现了中国第一次万米深潜。
在“探索一号”最顶层的驾驶舱里,当我试坐在船长的操作椅上时,一种时代的参与感油然而生。
回眸2016年,中国科学院几乎每个月都有“大事件”发生,而这其中,尤以一系列“上天”“入海”的重大成果最为引人注目。而作为一名科技记者,我也对自己能够亲历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深感荣幸。
4月6日,我国首颗返回式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成功发射,它是中科院空间科学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首批科学实验卫星中唯一的返回式卫星,也是迄今我国空间科学实验种类和项目最多的单次科学卫星任务。
7月18日,“探索一号”科考船带着中科院自主研发的万米级自主遥控潜水器“海斗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开展我国第一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活动,创造了我国无人潜水器最大下潜及作业深度纪录(10767米),中国深海科考从此进入万米时代。
8月16日,由中科院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它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对于我国实现从经典信息技术时代跟踪者向未来信息技术引领者的转变,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10月19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实现成功对接,“天宫二号”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牵头负责三大领域14项科学实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成功是中国人实现“航天梦”迈出的又一坚实步伐。
在采访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国家实力增强对科技界自信心的提振。近年来,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国家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为科技界放开手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我看来,这些成果与中科院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密不可分。比如2011年提出的“一三五”规划,2013年实施的院机关科研管理改革,2014年启动的“率先行动”计划等。如今,这些改革举措正真正从文件中“走”下来,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激发创新动力,让中科院充分发挥综合和建制化优势,整合全院乃至全国力量跨学科攻关,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科技工作者的拼搏精神也密不可分。在采访过程中,这样的身影随处可见。如“实践十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胡文瑞今年已经80岁了,但仍然躬身在卫星研制的第一线;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丁抗,在“探索一号”科考船的甲板上跟大家一起拉缆绳,带头践行“宁冒风险,不当逃兵”的万米科考精神……
“新生代”的表现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空间应用系统的很多关键研发环节,都是由“70后”“80后”科研人员完成的。在任务时间极紧、难度极高的情况下,他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用行动实现梦想,回击了社会上关于年轻人“空心病”的质疑。
但不知为什么,当回首这一年时,最让我难忘的却是一个细小的瞬间。
那是在8月12日,烈日当头的三亚,3岁小女孩李九月从母亲怀里挣脱,穿过鲜花与人群,与刚从“探索一号”船上走下来、皮肤晒得黝黑的父亲紧紧相拥。
在这一瞬,家与国融为一体。我相信,这个无比温柔的拥抱,会带给人继续前行的力量。

丁佳受邀在澳大利亚采访。
回归真实,才能真诚面对
■本报记者 李晨阳
2016年的不少报道选题,是围绕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和激励机制展开的。一天,一位接受采访的教授发给我一篇文章,说:“一生奉献的科学家没待遇、没名分,还得抛妻别子28年,知识分子的处境真让人伤心。”
我一看,他发来的这篇文章是《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文中写道:“整整28年,邓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卜,妻子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痴情等待。”我当即说:“老师,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我正在找寻这段往事的真相。”
今年夏天,报社领导将一个年度重大选题交到了我的手上——“邓稼先逝世30周年”。我掂了掂这个选题的分量,沉甸甸的,而我的心情也颇为复杂。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多都是从小听着“两弹元勋”的事迹成长起来的,“邓稼先”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岁月匆匆,一代巨人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这期间,许多人曾讲述他的故事,无数人从这些故事里收获过感动、思考和鼓舞。时至今日,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我能做的还有什么呢?没想到,正是这篇自2014年起便广为流传的,充斥着煽情的文章,给了我灵感。我决定不再复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伟大事迹,而是将笔墨聚焦一点:澄清那些围绕着邓稼先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传言。
不久,我一直在联系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邓公生前的工作单位,给了我回应。负责采访对接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吴明静老师告诉我,几位老先生在看过我的采访提纲后,纷纷表达了对其中一句话的兴趣:“对现有相关报道中一些以讹传讹的部分进行核实和订正,还原一个真实的邓稼先。”她说:“大家都觉得这实在太有必要了!”
这样的反馈,更坚定了我做这样一篇报道的决心。
分别在两个上午,我见到了我的两位采访对象:一位是邓稼先生前的学术秘书竺家亨研究员,另一位则是曾与邓稼先共事的原九所所长李德元研究员。两位年过八旬、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炎炎夏日专门赶来,为我讲述他们记忆中的“老邓”。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一些担忧纯属过虑。即便邓稼先的事迹已经传唱了30年,仍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格外打动人心。当曾经的那位秘书“小竺”告诉我,邓稼先为了请年轻的同事们一起看场戏,专门在戏场外找人要退票;当他带着满脸难掩的笑意,讲起邓稼先的饭盒频频被家鸡偷袭的轶事;当两位老人“老邓”长、“老邓”短地念叨着,无比亲切自然,并且骄傲地告诉我这种称呼是九所的传统时……数十载光阴渐渐隐去,一个可爱可敬,令人叹惋的邓稼先,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
采访临近结尾时,我很小心地问了李德元先生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邓稼先的功劳没有传说中那么大,是‘过誉’了,对此您怎么看呢?”
李老非常郑重地回答:“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团队确实人才很多,但是老邓的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稿件《邓稼先逝世30周年:还原真实才是最深的怀念》发表后,引发了一些读者的共鸣。当初与我探讨知识分子处境的那位教授第一时间转发了这篇文章,并且给我发了信息:“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报道!”一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则如此反馈:“细节真实感人,总算来了一次系统的纠偏还原。”
这次采访任务带给我内心深深的触动。对邓稼先的误读是一个寓言、一个缩影,折射了我们看待知识分子、看待科研人员的方式。因为那些有关邓稼先的扑朔迷离的传言,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谎言,它们更像我们在不同时代强加给科学家的种种幻想和迷思。这些被扭曲的视角,要么太过轻佻,缺少了对科研人员最基本的尊重;要么太过刻板,缺少了对人情人性最基本的观照。
反观我们这个时代不断追问的那些问题:应该如何理解科学家的贡献?应该如何对待科研人员?怎样重新审视脑力劳动的价值?怎样走出“重物轻人”的误区?这些聚讼不已的话题,都能从邓稼先的真假事迹之争中得到启示。
这篇稿件为我赢得了很多读者,我在欣慰的同时,也自知这与我的文笔无关。人们喜欢这样的文章,是因为大家呼唤真实的英雄,而英雄呼唤真实的评价和真诚的目光。
当我们看待科研工作者的方式,能够回归真实、回归客观、回归人性时,我们就能用更得体、更有效、更切合实际的制度,去支持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让更多科技工作者安心坦荡、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知。

李晨阳为神舟十一号接站。
《中国科学报》 (2017-01-01 第6版 元旦特刊)

